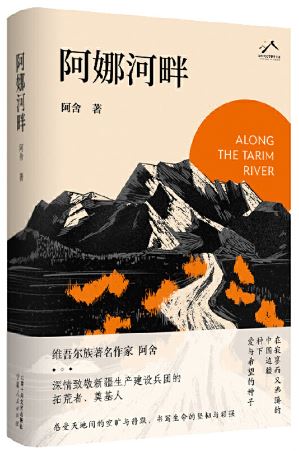
《阿娜河畔》,阿舍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宁夏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
“咱们场撤销了,划给了XX场,以后没咱们场了。”那是二〇一〇年的冬天,我已经不记得是谁首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而今唯记得的是自己的震惊,听完对方不甚明了的解释,电话这一边的我大张着嘴,像是喉咙里卡了一粒囫囵吞下的葡萄,生生憋出一串急速的心跳。
这意味着我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至少此后的中国地图或者新疆区域地图上,再也没了她的名字,她消失在中国西北角的大地上,如同一粒尘沙隐入了沙漠。就是这一年,我停下了那些关于回望故乡——一个兵团团场——的散文书写,而原本,我是打算在那篇刚刚荣获了一个刊物奖的作品《白蝴蝶,黑蝴蝶》之后,一鼓作气,牢牢抓住这块更能凸显自身的创作资源,像许多文学前辈与同道一样,像模像样地描绘和占有一个属于自身的“文学地理”。
一段时间过去之后,这个消息仍然令我难以消化,因为它在击痛我之余又变身成为一个隐形的冷眼——轻蔑地看着我,仿佛知道我心中的“小九九”,仿佛在傲慢地质问我——这下看你怎么办?
一停就是五年,五年里,我只字不写我的故乡,所发表的少数同类作品,都是之前已经完成曾一度被锁进抽屉的勉强之作。而这期间,我不能无视自己的感受,我得时常在心底面对那只“冷眼”扔给我的那个带着挑衅的蔑视:看你怎么办?当然,只能有一种选择:不能让这只“冷眼”得逞。于是,借着内心还未消散的疼痛感,我因由这个让我倍感受挫的消息,开始重新打量故乡,追问她一次又一次的命运从何而来。
凡事不会一次呈现它的本质。我由此获得了一个更广阔的回望故乡的视野。这个建在沙漠之缘的戈壁滩上、人口最多时达七千余人的兵团农场,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发展之后,于新世纪到来之际隐入历史。我对她的追忆再也不是自我的、碎片化的、怀旧式的、图解式的、浮光掠影式的,除了她对我生命的造就,她本身的命运与拥有,她肌体上的时代印痕,她迎接、养育和送走的人们,她的梦境与忧伤……犹如一幅徐徐摊开的画卷,在我眼前展开,并且从未如此使我全情投入。
她值得我去书写,这是她对我的赠予。她的建设者们用自己的人生与命运为时代和国家写就了一份特殊而珍贵的档案;她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她的反差——表面的荒芜偏远之下伴随有波澜壮阔的历史,沉闷单调的日常生活之下萌生着汹涌不息的心灵动荡;她的命运令人唏嘘,她的建设者们的命运更令人牵挂。理解到这些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2016年,经过五年的停滞,这时候再去回想五年前的那只“冷眼”,我的内心翻滚出诸般感慨,有怅然也有庆幸,更多是一种不吐不快的创作冲动——把故乡呈现在世人眼前,把那些无论是离去的还是留下的建设者从“远方”拉到人们的“眼前”,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与付出,了解他们的艰难与坚守、悲喜与挣扎。
问题是,仅仅书写故乡的历史是不够的,仅仅描摹那些建设者们的来来去去也是不够的。案头功课所花费的时间将近五年,这期间,除了按类别爬梳所需要的历史资料,我极少考虑小说该怎么去写,即便小说已经有了写作的大主题,我仍然深陷在“到底要写什么”的彷徨中。我问过自己许多遍——你真正想写的是什么?写农场历史的一曲三折?写建设者们的付出大于回报?这些均在其中,这些却都没有击中我心底那一连串的疑难与渴望,没能擒住那个创作冲动的核心。这些疑难不仅连接着故乡过去五十载的历史与命运,也指涉着当下我的生活以及每一个普通人眼所见身所感的现实。
故事将从新中国建设之初写到新世纪的来临,故事中人却经历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之久的中国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峰烟、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新时期激动人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巨浪裹挟着人的命运,也带来了参与者与见证者心灵的嬗变。这不仅仅是故事中人的故事,也是普通人的生活现实,是每一个将生命的热望贴在时代之躯上的普通人的心跳与呼吸。没有人能够离开时代,没有人不是时代的创造者和参与者,我和故事中人一样,经历着我的时代的风雨与彩虹。
小学五年级,学校把祖国和时代的未来放进了我的心中,那是一个远大的理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在一些郑重的时刻,我和同学们都会大声喊出这句话,并且坚信它的美好与光明,即便我从来没有想过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家里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我会变成什么样。而今,“现代化”已经成为眼睁睁的现实,从衣食住行到工作学习,再到抽象的思维与意识,已经在普通人生活中获得了全方位的合法性,并且改造着每一个人。对于我而言,“现代化”带来的最大改观在于它鼓励人对“自我”和“个体”的认知与建设,其次才是生活中那些令人欣喜惊叹的便捷与舒适。只是,诡异却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又随之眼睁睁地发生了,被“现代化”理念滋养了若干年的“个体的自我”在“现代化”车轮的超速行驶中反而渐渐丧失了“自我”,越来越多的人,也许我也身在其中,加入了数目剧增的“封闭的自我与个体”,于是,一再被强调的“自我”在慢慢失效,因为封闭的个体正借助“全球现代化”的速度迅速成为与“他人”类似的群体,并被淹没其中。当所有的人在强调自我的时候,自我也就消失了。现实来到这一步,那些孤立的个体,即使对此有所意识,也难以通过一己之力破除这种全球化时代的内卷。
对比故事之外我所感受到的处境,我并不觉得与故事中人的处境有多少不同,作为参与者,虽身处不同的时代,但我们有一个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人必将置身于自己的时代,必将被风浪所裹挟,然而作为个体的你将怎么办?你将使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即便所有的努力只是一场徒劳,你又该怎么办?所以,我所渴望的是——通过书写一个两代建设者的故事来呈现并保护住那些明净顽强的心灵。
在确定了要写什么之后,2020年7月,《阿娜河畔》进入写作,也许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在写作中发生叙述上的偏离,在那张画得乱七八糟的“茂盛农场场区分布图”上,我首先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一个人,应该如何处理与自我、他人、集体以及时代的关系?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哪一个选项能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自身变得越来越美好?
基于书写对象朴素顽强的底色,我选择了简单扎实的现实主义叙事策略,有意不去采取更多“现代性”的修辞手法,因为如果那样,会像给一位硬朗坚毅的农场建设者涂上红嘴唇那样可笑和不合时宜。也基于我对故事内外那些农场建设者们的敬意,我尽了最大努力,让小说的语言尽可能地饱含深情,以便能够匹配上他们的人生与心灵世界。
延伸阅读|好书推荐:《阿娜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