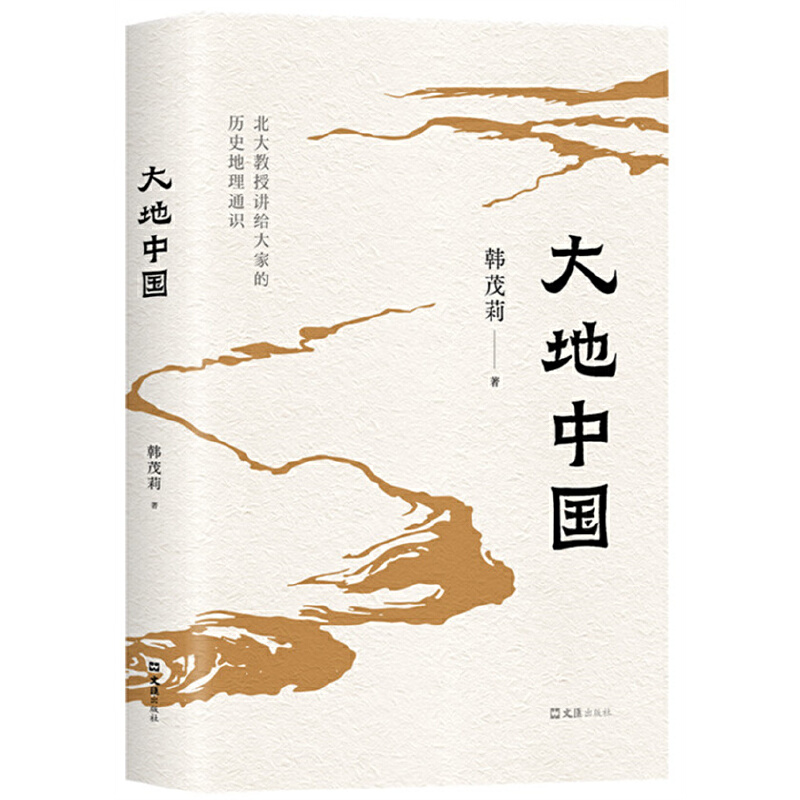
《大地中国》,韩茂莉 著,文汇出版社,2023年4月
多年前的一部纪录片《话说运河》,讲到长城、运河这两大中国古代工程,共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给我们留下无限遐思。“人字的结构,就是互相支撑”,也许出于巧合,也许隐含着必然,长城用于军事防御,而运河旨在运输,长城、运河这两项功能完全不同的工程,在过往的历史中以不同的姿态支撑着帝国伟业,且在大地上留下不灭的印记。
长城、运河都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工程,起始于不同时代,但都经历了王朝的兴亡过程。正是如此,讨论运河已不仅限于运输,那个时代、那段历史,或许更值得关注。
水路是世界上最廉价且便捷的运输形式。今天,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因地处大洲分界处、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闻名。然而,这两条运河的通航时间仅有一百多年,若以时间论,世界上最早开凿的运河其实在中国。史念海先生所著《中国的运河》告诉我们,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运河是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而事实并非如此,最早的运河出于楚人之手。那是楚庄王在位时(公元前7世纪一公元前6世纪),孙叔敖修筑堰坝,拦截沮水,开通了“通渠汉水、云梦之野”的运河,这项工程比开凿邗沟的时代早约一百年。自此之后,各地均有运河工程载入史中。
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一江春水向东流”营造了东西之间的舟楫之便,南北却缺乏天然水道,因此开凿运河联通南北不是单独一个王朝的举措。楚人开创了兴凿运河的先河,吴王夫差则通过邗沟、菏水两段运河沟通了江、淮、河、济四条河流,所有这一切均起步于春秋时期,自此之后的两千多年中,无论统一还是分裂,运河始终存在于历史的某个场景中。
千古运河,并非所有河段都为人所知,隋代那段与运河相关的历史尤为让后人难以忘怀,究其缘由,恐怕与隋朝短促的国祚有关。历代运河均为国家带来福祉,但隋代却因浩大的运河工程二世而亡,围绕其中因果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在历史学的视野中,运河已然成为政治的一部分。
运河的出现,首先改变的是地理。隋王朝建国后,隋文帝、隋炀帝先后开凿运河。隋文帝为了解决国都大兴城的运粮,于584年首先开凿了广通渠,自唐兴城堰(今陕西省咸阳市西18里)引水,渠道与渭水平行而东,至潼关入黄河。开皇七年(587年),他又主持“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其流径大体循邗沟故迹,北上抵达今江苏淮安。这段运河的开凿与南下灭陈、统一全国有关。此后,隋炀帝继位,开启了大规模开凿运河的工程,于605年开凿通济渠,由洛阳西苑引谷、洛水入黄河,又由板渚(今河南省荥阳市西北)分黄河水南行人淮,主要流经今河南省荥阳、中牟、开封、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安徽省宿县、灵璧、泗县,于盱眙北流入淮河。通济渠所经之地并非战国时期的鸿沟水系汳水(汴水)的流径,东汉年间,朝廷曾经对汴水水道进行过维护,至隋代因“汴水迂曲,回复稍难”而开凿了新的运河。尽管如此,原来的汴河仍然发挥着作用,故唐人白居易《长相思》有“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的诗句。608年,隋炀帝下令开凿永济渠,南引沁水入黄河,北上连接淇水,并于天津静海县与海河水系连通,最后止于涿郡(今北京市南,治所在蓟城)。610年,江南河开工,自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绕太湖东岸,经今江苏常州、苏州至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
铺在纸面上的地名背后,是一条将中国东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江河联为一体的人工水道,遑论一千四百多年前,即使放在当代,同样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然而,就是这样一项联通南北的大运河,却留下无数的骂名,后世不仅“尽道隋亡为此河”,而且将隋炀帝开运河目的归为游江南、观琼花,“种柳开河为胜游”。那么,隋炀帝耗尽民力,开凿运河的目的真是如此吗?
说起这个问题,离不开隋统一的历史。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了隋王朝,继而于589年灭陈统一全国,中国历史再度由分裂走向统一。
后人评述历史,总会提及秦与隋同属于实现国家一统的王朝,但统一后两朝的治国难度很是不同。秦人完成的是文化背景相同的六国统一,而隋王朝面临的则是南北胡汉之间的融合。自西晋“永嘉之乱”起,中国北方陷人十六国纷争。公元5世纪初,北魏统一了北方,南方自东晋以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几个政权的变化,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南北朝不仅是政权的对立,还存在着文化的不同,北方各个政权在匈奴、鲜卑、氐、羌、羯五个民族为主导的统治下,盛行以尚武为核心的异族文化,南方则完整地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当代人将文化视为软实力,这是说文化虽然不同于彰显国家实力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但决定着人心向背与对国家的认同。文化影响国民意愿,古今皆同。从“永嘉之乱”到隋统一,南北之间的政治分裂已近三百年,无论南北,对于彼此都很陌生。正是如此,隋统一之后不仅要致力于经济与国防发展,也要赢得文化认同,治国的难度甚于秦朝。
治国不易,完成天下大一统后的隋文帝并没有懈怠,洁身勤勉,励精图治,全力打造出万邦来朝、民生富庶的“开皇盛世”。然而,繁华之后暗流涌动,政治的一统并不意味着人心归附,尤其江南士族很难适应北方政府。开皇十年(590年),朝廷重臣苏威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五教”指五种伦理道德,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是朝廷推行教化的举措,本非弊政。即便如此,仍有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桧等举兵造反,自称天子,而“乐安蔡道人、蒋山李棱、饶州吴世华、温州沈孝彻、泉州王国庆、杭州杨宝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经此变乱,“陈之故境,大抵皆反”。虽然此次反叛被平定,但如何将南北真正联为一体,成为朝廷在意的一件大事。
隋文帝在位时,以稳定天下为先;隋炀帝承“开皇盛世”之基业,试图通过便捷的运河水道联通江南,改变“南服遐远”、南北疏离的局面,进而实现人心归服、国家认同。以国家政治为前提,开凿运河的浩大工程开启了。
赢得国家认同与民心归服或许是隋代帝王开凿运河的初衷,获取江南物资也不失为另一个原因。经东晋、南朝两百多年的和平发展,此时的江南一改往日的荒寂,已然成为“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之地,且“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2。用江南物产补国家用度之不足,凭借运河完成运输,再便利不过。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量,贯穿南北大运河的开凿,不仅有助于隋朝政权的巩固,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与社会进步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此毋庸看今天的论说,唐人即已有了中肯的评论。唐人李敬芳的《汴河直进船》有云:“汴河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李唐王朝是隋代运河的直接受益者,南北两大经济区的沟通促进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且成为北方政治中心所需物资的重要供给地,有力地支撑着政权的运行。
证明运河对北方经济贡献的实例是仓储。运河凿通之后,物资运送的中心是洛阳,隋代洛阳及其毗邻地区运河沿线均设有仓廪,其中河阳仓(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常平仓(又名太原仓,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黎阳仓(今河南省浚县)、广通仓(大业初改名永丰仓,今陕西省华阴市)、洛口仓(今河南省巩义市)、回洛仓(今河南省洛阳市)、含嘉仓(今河南省洛阳市)、子罗仓(今河南省洛阳市)均是国家重要的粮仓。唐代承袭了隋代仓廪的同时,又添设了新仓,并实行“缘水置仓,转相受给”的制度。众多粮仓不一一列举,仅以含嘉仓为例,即可以看出粮仓规模之大。含嘉仓为设在洛阳的国家官仓,仓有城,建在东都洛阳城北。考古界在仓城东北与偏南地区,勘探出大小不等的圆形或椭圆形地下粮窖287座,如果将铁路和建筑物下面的粮窖估算在内,仓城应有粮窖400座以上。这些粮窖窖口直径最大18米,一般为10~16米;窖深最大12米,一般为7~9米。每窖储粮五六十万斤,算下来仅含嘉仓储粮就达200万石,这与《通典》记载的数字基本吻合:“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这庞大的数字记录的,就是通过运河由南方输往北方的粮食数量,这坚实物质基础的支撑,为实现国家意志提供了保障。
隋炀帝时代开启的不仅运河一项大工程,营建东都洛阳、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三下扬州,这一切不仅耗尽了“开皇盛世”的物质积累,也将民怨推向高峰。朝廷兴修运河本意在于造福,但却因连年兴工、民不聊生而陷入罪责之中。
长城与运河共同构成的“人”字,从不同的角度支撑了国家基业,然而,运河带来的巨大的红利,隋人自己未及享用,王朝大厦便已轰然倒塌。隋朝因运河衰,因运河亡,将运河留给了后代。唐朝诗人李益置身运河两岸的喧嚣之中写下的《汴河曲》透出无限感慨:“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运河带来的种种繁华,隋炀帝再也无法感受,随同时光的流动,昔日的宫阙早已成尘、成土。
秦、隋两个从分裂走向统一的王朝,因长城与运河两项伟大的工程而影响后世,也因二世而亡令后人迷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其实,古人早已有了答案,水本可载舟,也可覆舟,水为民,舟为君,为君者一旦暴民取材,不施仁爱,以水覆舟带来的就是王朝的倾覆。秦二世而亡,“前车覆,后车戒”,本可成为后世统治者的明鉴,隋炀帝却“未知更”,因而重蹈覆辙,落了个二世而亡的结局。这正是唐人杜牧所叹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隋唐之后,随着都城位置从长安、洛阳迁移到开封、北京,运河的走向也不断变化。尽管运河的起点最终落在北京,但这联通南北的人工水道依然纵贯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隋炀帝身后一千多年间,运河上船来船往,人声桨声依然喧嚣,时间渐渐冲淡了历史的斑驳,留下的只是遗产。
延伸阅读|好书推荐:《大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