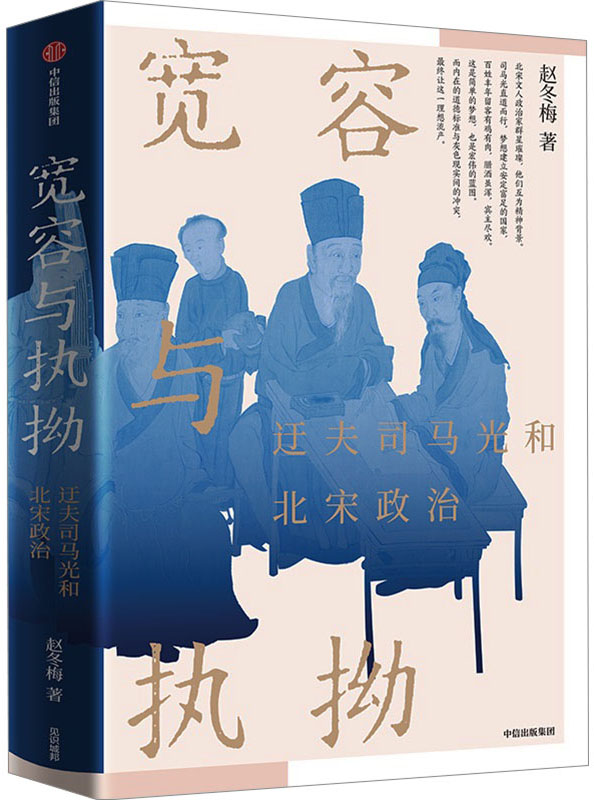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赵冬梅 著,中信出版社,2024年3月
至和二年,庞籍调任并州(今山西太原、文水等地);年底,司马光抵达并州,出任并州通判兼庞籍的机要参谋,直至嘉祐二年(1057)六月返京任职。就在这短短的一年半之中,发生了一件让他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伤心事。关于此事,在回到开封的一两年间,司马光逢人便说,想要解释,却无人愿听,无人能解;庞籍却终生不再提起,就像它从未发生。此事起初是公事、国事,是关乎宋朝边防、宋与西夏两个政权关系的大事;后来就变成了司马光与庞籍两人之间的私事,事关师生情、僚友谊;到最后,当所有人都选择遗忘,它便成为司马光个人的伤心事,深埋心底,烙印终生。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
这件事情一开始,是国家大事,司马光奉了庞籍的命令巡视边防。为了增强边境防御力量,司马光建议庞籍在宋夏边境增修堡寨。
作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庞籍负有统率边防驻军、组织防御、守土御敌的重大责任。在庞籍到任之前,宋朝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大部分屈野河西地的控制权。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去问麟州守臣,他们会说这是因为党项贵族的贪欲。新任党项首领谅祚(元昊之子)的舅舅没藏讹庞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他看中了屈野河西这块肥沃的土地,派人偷偷种上了庄稼,又把收获的粮食都拉回了自家(而不是西夏国)的粮仓。但这只是一部分事实,另一部分事实,麟州守臣是绝对不会坦白的。那是因为他们私心作祟、胆小怕事,没有尽忠职守。屈野河西地的伤心史就像是一部三幕剧。
第一幕,“职田争端”。屈野河西这块地,本来是宋朝政府的土地,租给老百姓耕种,收获所得归当地官员所有,作为职务补贴,这种地在宋朝叫作“职田”。麟州不是只有一名官员,知州之外,还有通判,还有当地驻军的统兵官。在职田的分配问题上,这些官员都觉得不公平。官司打到转运司,于是乎,最聪明的解决方案下来了:屈野河西地被宣布为禁地,“官私不得耕种”。干脆,谁都甭争了!宋朝方面放弃了屈野河西地的耕种权,一片好端端的肥沃土地要撂荒。
会撂荒吗?不会!宋朝的农民想种,党项的农民也想种。宋朝人赶着牛去耕地,党项人看见,立刻就上来赶,说:“你们官府都不敢种,你凭什么来?!”赶走宋人之后,党项人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侵占着屈野河西的沃野良田。这就是在“职田争端”之后上演的第二幕“蚕食记”。
如果拍纪录片,这时候画面上应该是生机盎然、等待开垦的土地,画外音应当是极度兴奋、充满希望的:“屈野河西地重新回到了大宋的怀抱!”但是,接下来上演的却是令人沮丧的“失地记”。
麟州守臣不敢或者说不愿意去管理、经营这块土地。有位负责任的武官曾经越过屈野河到河西去巡逻,结果,党项人还没怎么着,麟州守将却不干了,发来公文通报批评。从此之后,宋朝官方无人再敢过河。麟州守将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太简单了,宋和西夏已经讲和,党项人再贪婪,也不敢穿越六十里河西地,再跨过屈野河到河东来捣乱,宋朝的军队和老百姓不到河西去,双方就不会有任何接触,没有接触就不会有冲突。官员都是有任期的,只要在任期之内平安无事,官员们就是为国戍边有功,任满就可以提级。所以,麟州守将最关心的,不是屈野河西的领土是否遭到蚕食,而是河东的军民千万不要给他们惹事。宋朝军民不敢到河西去,六十里屈野河西地真正成了一块宋朝人的禁地。党项人当然不会让它空着,一年一年,春种秋收,一点一点,向东蚕食。
这出“失地记”上演了十年。庞籍和司马光到达河东的时候,党项人的实际控制范围距离麟州州城只剩最后的二十多里!当然,党项人所占据的那四十里屈野河西地,按照宋夏划界协议,仍然属于非法占有!但是,管他非法、合法,实际控制才是关键!
党项人对屈野河西地的蚕食,已经影响到了麟州的安全。青天白日,宋朝人在屈野河上捕鱼,党项人就敢上来驱逐追赶,扬言说“屈野河中线才是宋夏边界”。到了夜里,竟然有党项人越过屈野河,绕过麟州城,跑到麟州城东边去抢劫粮食、牲畜。宋朝的巡逻队追到屈野河边,就再不敢追了——追不追得到党项人事小,上峰怪罪下来,谁担着?1044年划定的宋夏边界本来在屈野河西六十里,由于宋朝官僚的失职、党项贵族的蚕食,到1055年,实际上已经东移到了屈野河一线,到了麟州城下!再这样姑息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庞籍决定整顿边防,收回屈野河西地。经营边防,对付党项人,庞籍还是很有一套的。他采取了四项措施。第一,命令宋朝军队重新开始在屈野河西巡逻,驱赶党项武装和党项垦荒队。第二,正式向西夏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西夏国主约束贵族,归还宋朝土地。西夏国主谅祚当时就是个几岁的小孩,侵占屈野河西地的大贵族没藏讹庞是他的亲舅舅,是抚养他长大的人。所以,想要让国主约束没藏讹庞,基本难以奏效。庞籍这么做,肯定也没指望国主的命令能起多大作用,主要目的还是引起西夏上层矛盾,并且在屈野河西地问题上表明宋朝的正义立场。第三,停止宋夏边境贸易,断绝对西夏物资输出。这是贸易战,很管用的一招。第四,派司马光巡视边防,筹划屈野河西地的最终解决方案。
司马光虽然反战,但绝不畏惧上前线。跟那些自己不敢过河也不让别人过河的官员不同,他亲自越过屈野河向西行进几十里,一直到达宋夏边界的白草平。肥沃的土地,芳草萋萋,静静地等待着开垦。这让司马光想到了庞籍的嘱托,感到了肩上的重任。守土之责,责无旁贷!是时候恢复大宋对屈野河西地的实际控制了!
陪同视察的麟州正副长官——知州武戡和通判夏倚向司马光报告,西夏人退兵之后,他们已经在河西修筑了一座堡寨。他们向司马光建议,乘胜扩大战果,继续向西推进,再修两座堡寨。武戡、夏倚向司马光保证,如果经略使大人批准,增派三千禁军、五百厢兵,禁军掩护,厢兵修筑,不出二十天,就可以修成两座堡寨。到那时,“从衙城红楼之上,俯瞰其地,犹指掌也”。从麟州衙门的红楼西望,三座堡寨一线排开,堡中有宋兵把守,西夏人有任何动作,都可以及时用烽火报告,直达麟州。如此,西夏人就再也不敢侵占屈野河西的良田了,修堡计划可以确保麟州以西五十里之内绝对安全。三座堡寨一线排开,堡中有宋兵把守,西夏人有任何动作,都可以及时用烽火报告,直达麟州。如此,西夏人就再也不敢侵占屈野河西的良田了,修堡计划可以确保麟州以西五十里之内绝对安全。
这个计划想要实施,必须征得经略使庞籍本人的同意,但是,毫无疑问,司马光个人是赞同这个计划的。他立即掉转马头,赶回并州向庞籍报告。回程之中的司马光油然生出参与创造历史的兴奋与自豪——在庞籍的主持下,在他的参与策划下,屈野河西地将要回到宋朝的怀抱。“春风得意马蹄疾”,在司马光的眼里,四周景物都变得温柔可爱,眼前有宽阔的路,胸中有涌动的诗。老天也帮忙,似乎有意配合他的心情。路过岚州宜芳县时,正赶上雨后初晴,青山含翠,草色欲滴,桃李争艳,司马光脱口吟出“满川桃李色,共喜传车还” 的诗句,那满川桃李似乎都在欢迎他巡边归来。
这样的好心情对在并州的司马光来说,实在是来之不易。
司马光是在至和二年年底离开山东,取道河北翻越太行山,进入并州的。他有一首《苦寒行》,描述的就是那次艰难的旅行,还有他初到并州的感受。起句云“穷冬北上太行岭,霰雪纠结风峥嵘”,一个“穷”字足见当时的艰难窘迫。太行山的路很窄,有的地方只能容一个人通过。按照宋朝制度,司马光此行携家带眷,随行的有他的独生子,还有张氏。大风雪之中,小孩子冻得直哭。做母亲的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张氏自然是愁容满面。由于对旅途环境的恶劣估计不足,干粮带得也不够,仆人们总是在喊饿,马也是瘦的,看着一点力气也没有,石板路滑,马失前蹄,吓得人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而这冷汗在人身上都冻成了冰。
“万险历尽方到并”,人到了并州,司马光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作冷得“惨烈”。“阴烟苦雾朝不散,旭日不能复精明”,整个早晨都蒙在雾里,太阳好像根本就出不来似的,人的心情一下子就降到了冰点。“跨鞍揽辔趋上府,发拳须磔指欲零”,骑马去府衙上班,头发冻成了卷,胡子感觉一碰就断,手指头好像就要掉下来,冷啊!好不容易进了办公室,仍然是冷,“炭炉炙砚汤涉笔,重复画字终难成”,砚台里结了冰,要放到炉子上烤,笔头也冻得生硬,要用热水泡软了才能写,可还是描来描去不成字。天太冷,想要喝口酒暖暖,“谁言醇醪能独立,壶腹迸裂无由倾”,酒壶也冻裂了,哪儿还有酒啊!这就是司马光初到并州的感觉,寒冷愁苦,一点儿新官上任的兴奋都没有。不是司马光对并州有偏见,而是当时的并州冬天实在太冷,根据竺可桢先生对中国古代物候资料的研究,宋朝正处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寒冷期,气温普遍比现在要低,所以,那时的并州比现在要冷得多,而那时人们的保暖御寒能力也比现在要差得多。
除了冷,让司马光感到不适应的还有“老”。就是在刚到并州的这一年,三十九岁的司马光第一次在自己的头上发现了白发。尽管司马光自我安慰说 “我年垂四十,安得无华颠”;他鼓励自己勇敢面对,坚持不拔那几根白发,要留着它们时时提醒自己切勿虚度光阴,“留为鉴中铭,晨夕思乾乾”;然而,毫无疑问,他的心里是有一点发虚、有一点担忧的,“所悲道业寡,汩没无它贤。深惧岁月颓,宿心空弃捐”。司马光的长处是批评,是匡正,是做皇帝和朝政的忠诚的监督者。最适合他建功立业的地方是朝堂,不是地方;最适合他发挥才能的是高层政治、大政方针,不是按部就班的公文。居庙堂之上服侍皇帝,是司马光的“自我期许”和“自我设计”。他本来离那个目标已经很近了,只是因为庞籍罢相的关系,他才离开了皇帝,离开了首都。从开封到郓州,再到并州,快四十岁了,他却离朝堂越来越远。端详着铜镜里已经有了白发和皱纹的中年男子,司马光心里怎么能够不起急,怎么能够不焦虑?
当然,司马光并不后悔到并州来。他来,就是为了报答庞籍的知遇之恩,“我来盖欲报恩分”,他愿意为知己者死。恩师老了,又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身边必须有人照顾。为了庞籍,哪怕冻死边城,司马光也不会说一个“悔”字。但是,除此之外,他看不出自己在这寒冷的边城还能够有什么作为。这才是让司马光感到沮丧的症结所在。对理想主义者来说,最痛苦的是什么?不是没有工作,而是看不到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到并州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几个月,司马光虽然对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但情绪却始终不高。这种情况在嘉祐二年春视察屈野河西地之后,发生了真正的逆转。在那片沉睡的土地上,司马光看到了边疆工作的意义。当他在麟州州衙的红楼上向西远眺,当他跟麟州守臣商讨屈野河西地的收复计划,在那一瞬之间,他放下了自我,不再执着于在朝廷建功立业的自我设计,他的胸中激荡着在边疆参与创造历史的自豪感。
在屈野河西地增筑堡寨,让宋朝的存在成为事实,让那一片草长莺飞的土地成为宋人春种秋收的沃野良田。这美好的图景让司马光感到欢欣鼓舞。他快速赶回并州,向庞籍做了报告,庞籍很快就批准了司马光的提议,并且用公文通知麟州准备动工。如果这一切能够实现,那么,司马光的个人履历将写下重要的一笔。但是,这种乐观昂扬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太久,屈野河西地收复计划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很快,司马光和庞籍就被甩入了麻烦的旋涡,国家事、边防事也转变成了这一对师生之间的感情事、司马光毕生的伤心事。
延伸阅读|好书推荐:《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