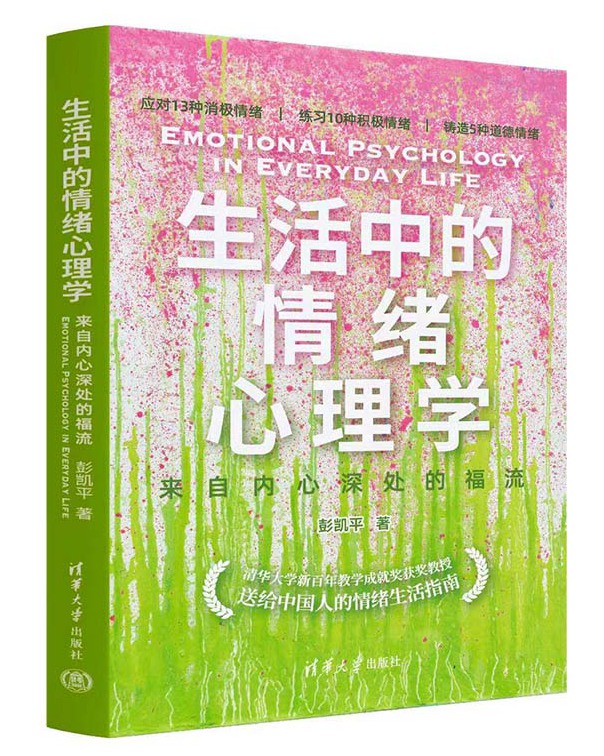
《生活中的情绪心理学:来自内心深处的福流》,彭凯平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
一位抑郁者的觉醒与自救
我的一位朋友,曾用15年的时间积累起上亿财富,衣着光鲜,事业有成。然而,当一场金融风暴席卷全球,42岁的他一夜之间回到赤贫,豪车、别墅被拍卖。随后他抑郁了,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在一点点流失和衰败。然而,他不敢去看医生,一方面,害怕会被确诊;另一方面,也害怕被熟人发现。一想到大家知道他得了抑郁,会为他感到好奇、惋惜时,他就宁愿让自己在这样的痛苦中沉沦下去。
有一次他来上我的课,寻求我的帮助。当时我正在国内传播积极心理学,深知情绪的替代和升华的意义。我没有引导他回忆让他陷入抑郁的过往场景,也没有帮他探究原生家庭的罪过。我只是反问他:“你看你都活不下去了,都要自杀了,难道不应该回家去见父母最后一面吗?”
他说:“对啊,我都要死了,确实应该回去和父母告个别。”
他的回答让我内心有一点安慰,我感觉他很有可能走出抑郁。
从他的描述中,我了解到距他的家两公里处有一座林场,林场里有很多刚刚锯下来的粗树干。
我建议他:“回到家,给你一个任务,做完这个任务,你和父母的缘分就尽了,你可以安心地去另一个世界。这个任务是你请母亲帮你将30根粗树干从林场搬到院子里,什么理由都可以。”
这位朋友是个执行力很强的人。上完课,他真的飞回老家照我的办法去做。一年后,当我再次见到他,他已经脱胎换骨,神采飞扬,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此时,我知道他已经彻底走出了抑郁情绪。
为什么会有如此惊人的转变呢?下面的这段文字来自他的回忆录,给出了答案。
我回到家,步履沉重,只想着赶紧完成任务,和母亲早点告别,快点离开。
母亲看我回来,特别高兴,她的白头发比去年又多了,步履也有些不稳。看着她欢快的背影,我一阵心酸,在心里默默地说:“妈,你唯一的儿子今天来见你最后一面,你一定后悔生了我这么一个儿子吧。”我不忍告诉她,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和她告别。
我编了一个合理的谎话:“妈,从林场买30根大木头吧,这次我在家待的时间长,我想做点木工活,打点家具。”母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以为这次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我交代母亲:“我午睡起来,帮你一起去把木头装车拉回来。”
那天,我一觉睡到下午3点,睁开眼,心情依然沉重,烦躁得很。我走到窗前,已然将中午的话忘到了九霄云外。
突然,透过窗户,我看到一个瘦弱的身影,抱着一根比她的腰还粗的木头,艰难地挪动着。那是我的母亲,此时,她已经70岁了。此刻,她还不知道她唯一的儿子已经打算要离开人世,离开她。
那一刻,我泪如雨下,不能动弹。我只是提了一个要求,70岁的母亲竟然真的努力帮我实现。我以为,难过的只有我自己,却不曾想,实际上,我的崩溃也是对她的折磨。
我看着她一根一根地把木头拖回来,放在空地上,一趟又一趟。
我没有去帮母亲。我知道她想为自己的儿子做点事。
就这样,我站在窗户边,终于抑制不住,趴到床上号啕大哭。那一天,我终于理解了什么是“为母则刚”。
不知过了多久,我擦干眼泪,走向母亲。
她正坐在地上,汗珠映得她的脸更加红润了。晚霞火红,炊烟袅袅升起,这情景很熟悉,很温馨。突然一下子,我的头脑明亮起来,神清气爽,过往的痛苦抛在脑后。我知道我走出了抑郁。
看到这段描述,我会心一笑,也许这就是心理学的奇妙之处。
建立亲密关系
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理论,叫作恐惧管理理论,由美国堪萨斯大学的3位心理学家——杰夫·格林伯格、谢尔登·所罗门、汤姆·匹茨辛斯基在1984年共同提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每个人都有对死亡的恐惧心理,为了缓解对死亡的恐惧,人们创立了文化世界观。文化世界观可以使人们感觉象征性地超越死亡,可以给人提供一种感受,即每个人都是这个有意义的世界中有意义、有价值的一员。恐惧管理理论提出了自我心态保护的两种机制——近端防御机制和远端防御机制。抑郁情绪的管理也有近端防御和远端防御。近端防御就是自我暗示、自我激励,找到自我心理调节的技巧和方法,比如说深呼吸、打坐、冥想等;远端防御则是让一个人逐渐形成自己的积极人生态度。帮助这位先生走出抑郁的首要法宝,是建立亲密关系,这是能够让自己开心的远端防御机制。亲密的人际关系刺激催产素,瑞士苏黎世大学费尔教授第一个发现催产素对积极情绪的促进作用,无论是母爱、父爱,还是兄弟姐妹的支持,都可以让人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哈佛大学研究团队曾开展过一项长达70多年的追踪研究,为发现哈佛的毕业生中谁会成为人生赢家。追踪结果显示,真正决定一个人成功的因素,不是大学专业,不是学习成绩,而是美好的关系,包括稳定的家庭关系、亲密的朋友关系等。所以,关系不仅是我们人生幸福的关键因素,也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法宝。
哭
哭是走出抑郁情绪的法宝之一。
哭是好事,为什么?因为哭除了能释放让人心情振奋的催产素,还会产生内啡肽,也有令情绪愉悦的作用。举个例子,辣味会在舌头上引发痛苦的感觉,为了平衡这种痛苦,人体会分泌内啡肽,消除舌头痛苦的同时,在人体内制造了类似于快乐的感觉。尽管哭是表达痛苦的一种行为,但哭也会刺激人体分泌内啡肽,因此说,引导陷入抑郁情绪的人放声大哭,可能是一种非常好的疗愈方法。
然而,在社会文化的潜移默化中,很多人已经很久没哭过了。
美国心理学会发布了一项调查数据,2020年美国的男性大概每个月哭两次,女性大概每个月哭四次。这说明哭有一些性别差异,但这个差异与后天文化的滋养脱不开干系。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孩从小被教育不应该哭,要表现得很坚强。这种误区全世界都有,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对哭有偏见,特别是男性的哭被视为软弱无能或情绪障碍。
其实,在心情抑郁的时候,哭一哭,是对自己内心抑郁情绪的一种释放。因此,我常开玩笑地说,人啊,最好一个月能哭个三五次,哭一哭更健康,令情绪彻底释放。如果你不想让别人看见你的眼泪,不想让人看见你的脆弱,那就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地抹抹眼泪。你会发现,哭过之后,你的世界海阔天空。
身处失败和逆境,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抑郁。面对抑郁,不同的排解方法会带来不同的命运。
冥想、运动、写作
走出抑郁的法宝有很多,冥想、禅修、运动对调节抑郁情绪都有很大的作用。然而,要瞬间从抑郁的状态调整到积极的心态不太容易,也不现实。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自己需要调整心态,并学会观察与反思自己内心的一些真实反应。例如,写作就是自我沟通与反思的过程,对战胜抑郁效果明显。抑郁时,会感觉很多事情失去了控制。当我们开始写作时,会不自觉地谋篇布局。“谋篇布局”增强了我们的控制感,这种控制感可以促进血清素的产生,让我们身心愉悦。写作还可以改变抑郁者看问题的角度。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写 作时,我们会从当前的事件中跳出来,保持中立的态度,会有严谨的思索、深入的批判,这样就可以找到困扰的症结所在。
那么,如何写才能产生更多的积极力量呢?
第一是多写。写作是倾诉,不是评判,不是比较。把烦恼写出来,就像是和朋友倾诉,烦恼得到宣泄。写得越多,心情可能越好。
第二是坚持写。争取每天写20分钟,20分钟是刚刚好的时间。也可以试一试新的写法、新的表达,尽量运用积极正面的语言去鼓励自己,给予自己肯定。
第三是别把写作当作一件大事,不要难为自己。其实写作不是一种工作,不是一种挑战。如果写作对于你来说不再是一种放松,而是一种折磨,那就要果断放弃。
“睡道”至简
另外,睡眠问题几乎是困扰所有抑郁者的一大难题。在我看来,抑郁的烦恼是可以睡好的,至少有一半的烦恼是可以通过睡眠消除的。
很多人在睡觉时,采用“数羊”的方法来减轻自己的失眠。这个方法来源于西方,目的是在一种节奏中慢慢进入放松状态,逐渐入睡,类似于催眠疗法。但我发现数羊并不太适合中国人。羊的英文发音是“sheep”,睡觉是“sleep”,英文发音很接近,所以,在英文语境中,数羊就好像是说让自己睡觉。而咱们中国人数羊,发出的声调是高亢的,是向上的,越数就越兴奋: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可能数到两千只羊,还没睡着。而且数数会让人的精力都集中在数字上,只会让人越来越清醒。
那么有什么办法,让我们中国人也能安然入睡呢?受到数羊方法的启发,我们发现了一个促进睡眠的谐音法。老外是 “sheep,sheep,sheep”就睡着了,我们可以“谁,谁,谁”, “谁”与“睡”谐音,也许很快就能入睡了。建议大家不妨试一试这种新的适合咱们中国人的数“谁”的方法。
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帮我们入睡?正念可以让我们快速入睡,想象自己睡在一棵非常漂亮的树下或者一片草地上,想象自己带着快乐的念头入睡。正念是常用的入睡技巧。
总而言之,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遭遇或轻或重的抑郁,如何对待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健康,甚至是会影响我们一生。就算已经抑郁,跌入了人生低谷,也要向上走,这就是积极心理学的积极意义。
延伸阅读|好书推荐:《生活中的情绪心理学:来自内心深处的福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