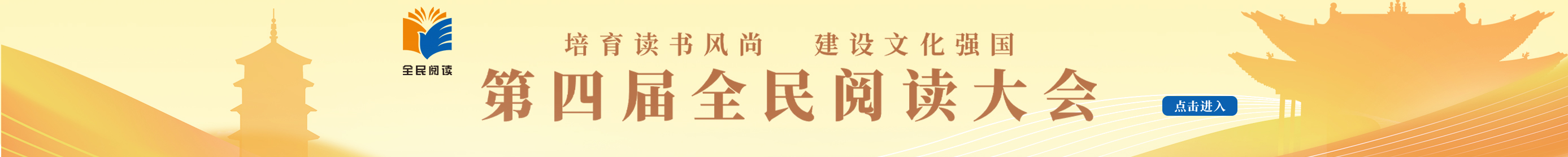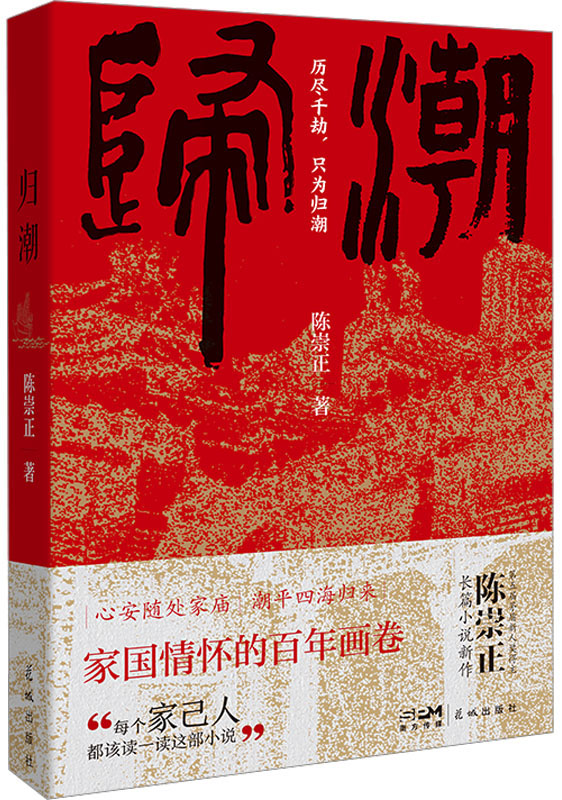
《归潮》,陈崇正 著,花城出版社,2024年3月
1
陈洪礼缺席了林汉先的葬礼,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坊间也有诸多猜测,后来大家才从黑珍珠的口中得知消息,陈洪礼病倒了。不是装病,而是真的呕血,医生诊断是胃出血,说幸好送来及时,不然就麻烦了。
病情稍微稳定之后,陈洪礼就带着黑珍珠和十岁的海福来到林家,一路上他一直扶着黑珍珠的肩膀,差不多将她当拐杖。这一次林阿娥没有赶他走,还给他搬来一把椅子,因为陈洪礼整个人瘦了一圈,瘦得触目惊心。一个人的话语和行为都可以伪装,但身体是如此诚实,陈洪礼用一场九死一生的病,获得了林阿娥的谅解。林阿娥让雨果给洪礼伯伯倒茶。陈洪礼摆摆手说不用,他指了指黑珍珠手里的水瓶说他喝不了茶,还得继续吃药。
陈洪礼开门见山:“听说你要将汉先的骨灰带回碧河梅山?”
林阿娥点了点头。
“能不能等以后世界太平了,再送回去?”
林阿娥摇了摇头,眼神中透露着坚定,近乎病态的坚定。
陈洪礼哦了一声,这场病让他显得迟钝。这样的冒险意义何在?他想不清楚,只知道已经无法阻止眼前的林阿娥,这个完全笼罩在悲伤之中的人,脸上有令人心碎的苍白。如果一个错误已经无法改变,那么只能尽力去减少代价。他想了一会儿才开始说话,主要表达三个意思。其一,他跟英顺伯通过电话,研究了路线,认为现在还是得从海上绕道,经槟城往西贡,再进入云南,那边的滇缅公路现在依然畅通,到了国内再自西向东进行,前半段英顺伯会通过关系提供保障,但后面就非常艰险,完全无法预料。其二,原来的陶瓷骨灰罐太重,也易碎,路途遥远,建议分装在两个铝盒里,更加轻便有利于行动,安葬好汉先及时返回。其三,最好将林雨果留在曼谷,以确保小孩安全。
林阿娥对他们细心周全的考虑表达感谢,然后说:“路线听从你们安排,骨灰分装也同意,安葬时合在一起便是。至于雨果,我是一定要带走的,汉孝也会跟我一起回去。这个事我们已经商量了几次,最后我们假设汉先还在,也参加家庭会议,他应该会说,生生死死,一家人总要在一起。至于能否返回曼谷,这个要看上天的安排,但如果汉先还在,问他的意见,他应该会主张我们埋在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上。汉先早在几年前就一直希望我们能回到潮州去,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何要把我们赶回去,但这些天我似乎有点明白,他似乎能够预知自己何时归天。我说不清楚,他有时候也是那种非常神道的人。我们见过太多的人客死他乡,总是习以为常,但对于汉先来说,碧河边那片土地上,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在牵动他,让他回去,我好像慢慢理解他在想什么。这几天我每晚都能梦见他,这样的梦让我非常开心,我知道路途凶险,只能祈求汉先在天之灵能保佑我们。”
房间里只有林阿娥的声音,等她的声音停了下来,陈洪礼才深深吸了一口气。他说,他也预料到林阿娥会这么决定,也好,坏人的眼线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八方楼林家,回国不见得更危险,在这里也不见得更安全。他转头问汉孝未来的打算。林汉孝说,之前跟两个哥哥学了一阵子开车修车,技术一般,但想着总比那些什么都不懂的强,送嫂子回到碧河镇,然后便去找三哥,上阵杀敌他或许不行,但搬货做后勤还是可以的。
陈洪礼拿出两个铝制的方形盒子,说这盒子轻便坚固,可以用来装骨灰。他说如果可以,他建议由他来做这件事。
林阿娥点了点头。陈洪礼其实什么工具都准备好了,如何分装安放在背包里,他都考虑妥帖。他打开骨灰罐,喃喃自语:“你从小就怕痛,我尽量慢一些。”
临走的时候,陈洪礼让大儿子陈海福拿出礼物,送给林雨果。是一对长命百岁白银脚环,上面布满了吉祥的纹饰,也配有小铃铛,只是不响。林阿娥一边表达感谢一边说:“雨果八岁了还戴脚环不合适吧?”陈洪礼说:“主要是辟邪保平安,我想了很久,戴脖子和手上的饰品都不合适,还是戴脚上,万一遇到困难,典当了可以应急。”他希望林阿娥先给雨果戴上。林阿娥接过来,正要戴上,又在手里掂了掂重量,左右端详了一下,说:“你洪礼伯伯这礼物很贵重啊。”陈洪礼说:“就知道瞒不住你,只是出门在外,一切低调行事,贵重算不得贵重,用了点心思罢了,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林阿娥叹了口气道:“汉先常说你心思缜密,事故时你若在八方楼,提醒一下,可能也不至于酿成那样的祸事。”
陈洪礼说:“人算不如天算,我又何尝不被命运捉弄,你们路上一切小心,到了国内务必给我来信,但凡我能帮得上忙的,也请一定告诉我。曼谷这边,林家带不走的物产我会代为看管,等以后交还给你们;汉先没做完的事,我会替他去做。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会就这样不明不白结束,那些助纣为虐的汉奸,总会遭到报应。”林阿娥见他说到激动处气喘吁吁,于是说:“坏人自有天谴,还是保重身体要紧。”
2
按照英顺伯的安排,汉孝去筹赈会报名参加回国的机工队伍,林阿娥和林雨果作为随行人员前往。那几天,得知消息的亲友都来送别,其中有个看起来有点眼熟的女孩来见汉孝,眼睛都哭肿了。
黑珍珠跟林阿娥解释,说汉孝唱戏,把那姑娘迷得神魂颠倒。姑娘姓杨,祖籍潮阳达濠,家产殷实,杨姑娘的父亲实在见不得女儿整日以泪洗面,于是给林汉孝提出三条路:第一条路是跟姑娘成亲,条件随便提;第二条路是可以暂时不结婚,给两间铺头让林汉孝做橡胶生意,家族会尽力扶持,不成功也会做成功;第三条路是如果喜欢汽车,杨家有货运卡车二十辆,可以让林汉孝去开一家货运公司。但三条路林汉孝都拒绝了。他对姑娘说,如果家中没有变故,哪一条路都无所谓,随性而为,人生本来就不需要规划;但如今不同了,长兄去世,嫂子决定千里归葬,长兄如父,从前老是不听兄的话,现在兄死,总要听一次话。姑娘听后为之动容,想跟着汉孝回国,但家里不肯,父亲下了通牒,如果跑了就永不相认,杨姑娘于是退缩了。
和这世上大多数有而不得、无疾而终的爱情一样,情意绵绵的两个人最终只能在泪水中告别。汉孝看着杨姑娘哭着从林家离开,内心酸楚无法言表。林阿娥跟汉孝说,如果喜欢这个杨姑娘,也可以留下来。林汉孝说,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喜欢。在他二十五年的人生经历中,他一直是那个最被动的角色,他唯一一次主动求索,是学唱戏。他觉得自己在戏曲的想象之中更能获得感动,而在现实中,他木讷内向,他连自己都不喜欢,如何去喜欢别人。
葬礼之后一个多月,过了霜降,林家三人终于还是上了南线铁路,第一个目的地是槟城。隆都弟翁如棋将他们送到车站,才发现车站有很多亲友等在那里,其中有些并不相识,只是从前受过林汉先的帮助,前来拜别。林阿娥和他们一一握手,她知道许多人见了这一次,此后余生便不再相逢。
林阿娥本来以为这是一次秘密行动,到了槟城,她才知道英顺伯和陈洪礼已然将她的行踪告知所有途经站点的华侨组织。临行之前陈洪礼跟她通过电话,他说,根据情报,日寇特务组织一直对他们三人进行盯梢,他和英顺伯都认为,此行只有大张旗鼓,引人注目才更为安全。行在光明中,特务更不好下手。她现在明白了,所谓大张旗鼓并不是一个比喻,而是真实的。他们在槟城,从车站到下榻的天天酒店,一路上都有华侨接送,他们甚至打着横幅,上书:历尽千劫,只为归潮。林汉孝认得这句话,他说这是孟先生从前说给大兄汉先和陈洪礼听的话,如今竟然成为一次行动的标语。
接站的人虽然不多,但林阿娥并不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为首的人姓蔡,饶平人。蔡先生握着林阿娥的手,说和汉先先生是老朋友,以前羽先生多次带着汉先来槟城:“汉先先生是我辈楷模,他和羽先生热心救国的事迹我们在华语报纸上读过,感人至深。”这样的阵仗让林阿娥吃惊,她还不知道如何去扮演一名壮烈牺牲的勇士的家属。对她来说,她认识的林汉先一直都是普通的,没有任何光环的。不过她很快也进入了角色,她跟自己说,也许一个人死后,就需要有光环去感召更多的人。只要对国家抗战有利,那么,一次本来是痛苦的,完全属于内心完满的旅程,被装饰成充满聚光灯的星光大道,她也可以接受。“这样的礼遇,就当是八方楼送给汉先的礼物吧,毕竟他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八方楼。”在酒店入睡之前,她对着洗手间的镜子自言自语。
林汉孝在槟城和他的机工队友会合,一行人乘船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也是一样,标语,接待,媒体报道,这里甚至比槟城更加热烈,人也更多。这次迎接她的人姓黄,黄先生说汉先多次在他家中留宿,喝酒聊天到天亮,他们都是摄影爱好者,常常通信商量如何将华侨捐赠的物资运到家乡。
这次林阿娥说着便哭了起来,痛陈日寇的卑鄙无耻。有记者问躲在林阿娥身后的雨果,林雨果并不清楚记者的问题,她还听不懂,但她很聪明地说了一句:“我恨日本人。”记者又问:“你叫什么名字?”林雨果说:“我是林汉先的女儿,我叫林雨果。”这个镜头又被记者记录了下来,母女俩的照片登上了报纸,旁边还有黄先生,他们握手交谈,十分自然。新闻标题竟然变成《我是林汉先的女儿,我叫林雨果》,里面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民族危难奔走者,不可使其殒殁于无声。”文章痛斥日寇如何迫害侨领,其中林雨果被绑架那一段描写读起来比记忆中更为扣人心弦。夜里,看着熟睡的林雨果,林阿娥捋着她的头发,喃喃说道:“你是好样的,也是幸运的。”熟睡的林雨果看起来更娇小可爱。在林阿娥看来,她的女儿才八岁,就可以在报纸上成为讨伐敌人的利器,有多少在战火中委屈死去的小孩,并没有女儿这样的机会进行控诉。
延伸阅读|好书推荐:《归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