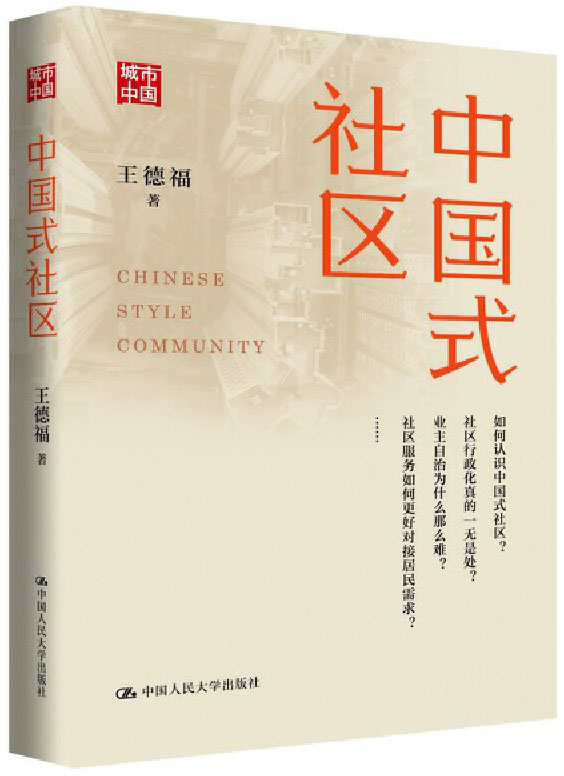
《中国式社区》,王德福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
高密度居住
高密度居住空间是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必然选择,以尽可能利用有限的土地承载更多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后早期的低层(1~3 层)或多层(4~6 层)高密度职工新村、单位小区,到21世纪以来主流的高层、超高层高密度小区,无一不是高密度住区。
高密度居住带来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拥挤效应”。现代大城市的拥挤已成为常态,无论是上下班高峰期的道路拥挤,还是节假日商场、广场、公园的人员拥挤,都让我们在享受现代化城市生活的便利性的同时,不得不忍受与更多的人挤在一起,拥挤已成为“城市病”的代名词。而从居住区来看,拥挤意味着上下班时的电梯拥堵,意味着小区公用设施更高的使用强度,意味着频繁忍受他人行为带来的负外部性。拥挤对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它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居住和家庭生活的私密性、舒适性的需求。从拥挤的城市道路和公交地铁上回到家里,人们渴望的是不受侵扰的身心放松:关上房门享受私密生活的自由与惬意、温馨与甜蜜,或者到小区花园、广场享受与家人一同活动的亲密和放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小区内的社交需求会降到最低,陌生他者的介入往往会变成不礼貌的侵扰。处于私密居住空间中的时间是那么有限而且宝贵,这就使得任何侵扰都变得不可忍受,而人们对侵扰的反应也就很容易变得急躁和粗暴。
群体的陌生化会放大这种拥挤效应。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人际互动预期长久且稳定,人们对社会支持的需要又会强化地缘关系的重要性,亲密交往的功能需要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私密生活的需要。在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空间中,无论是交往预期还是社会支持需要都大为弱化,而人们对生活私密性和自由性的需要则会压倒对亲密的地缘交往的需要,亲密交往则更多安排在居住空间之外的城市公共空间中,通过血缘、业缘关系来实现。在一个拥挤的熟人社会中,人们基于长久的交往预期和社会支持的需要,会对生活交集中的接触与摩擦有更高的耐受度,个人行为也会更多考虑到机会成本问题,社会舆论、群体制裁才会成为可能。而在拥挤的陌生人社会中,这种耐受度会显著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更低,人们往往更容易走极端,要么自我而冷漠,关起门来过日子,要么暴躁容易冲动——蝇头小利都会变成意气之争,互不相让,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很容易扩大化,变得难以收拾,非要分出个是非对错。
复杂邻里
高密度居住带来的另一个典型问题是复杂邻里。邻里关系也就是地缘关系。中国人常讲“远亲不如近邻”,这是对集体生存经验的总结,意思是邻里关系是最便利的社会支持网,可以帮我们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在流动性极低的乡土社会中,地缘关系具有先赋性和不可选择性,社会交往必须在给定的地缘关系网中展开,人们就倾向于维护这种关系。随着社会流动增加,地缘关系最先受到冲击,其可选择性渐渐凸显出来。在城市社会中,地缘关系在人们社会支持网中的作用趋于边缘化,亲缘、业缘与趣缘关系更为重要。正如上文所说,地缘交往的内在动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大型集合式空间与高密度居住形式,共同塑造了陌生人社会邻里关系的特点,我称之为“复杂邻里”。它具有“一低两高”三层内涵:一是社会关联度低。人们对地缘关系的社会支持需要弱,社会交往频次少,且有限的交往也大多只是单一交往,不可能产生乡土社会那种附着了人情关系的深度交往,也就很难形成社会关系网,不能发育出社区性的社会资本,彼此的社会关联程度比较低。二是生活关联度高。一方面,日常生活中共同使用小区共用设施设备和公共空间时,必然发生互动和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居家生活时也要受到上下左右邻居的影响,比如楼上楼下的漏水、噪声问题,房屋装修改造造成的承重结构问题,阳台滴水问题,等等。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不得不产生相互影响。三是关系脆弱性高,即邻里关系很容易因为利益分歧和冲突而破裂。原因很简单,社会关联度低,就造成邻里关系缺乏功能依赖的长期稳定预期,缺乏由此形成的人情润滑和维系,一旦在生活中发生利益碰撞和冲突,双方都倾向于一次性计算和分清是非对错,很容易导致关系永久性破裂,且缺乏社会性的关系修复机制。这就是邻里关系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一方面,日常生活需要共处;另一方面,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足以独处“,互不相关”。显然,如果是独立住宅和小型社区,邻里关系就会是社会关联度与生活关联度都很低的状况,就不会产生如此明显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延伸阅读|好书推荐:《中国式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