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燮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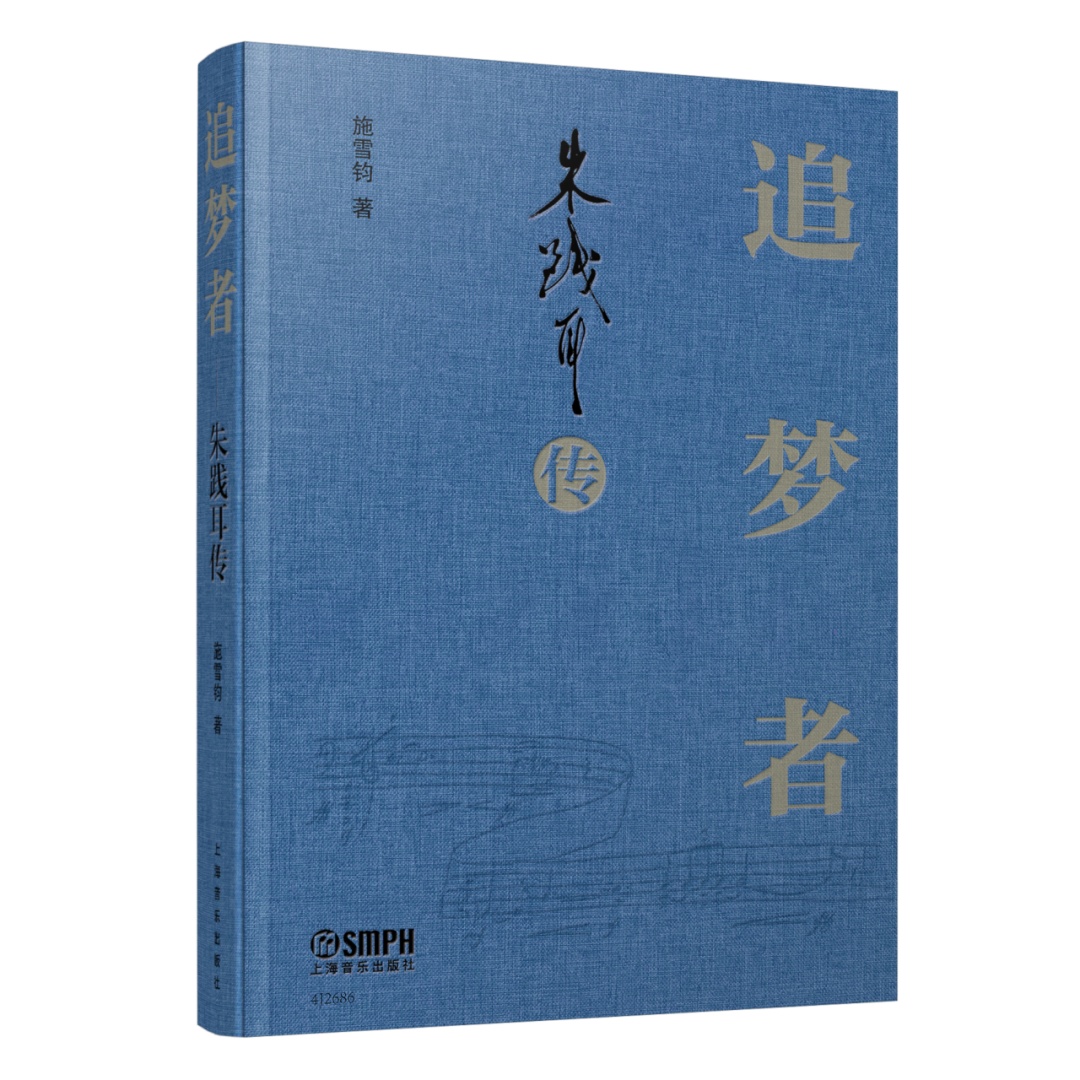
《追梦者——朱践耳传》,施雪钧 著,上海音乐出版社,2024年10月
历经五年,雪钧先生终于完成了《追梦者——朱践耳传》的写作。作为第一读者,我一口气读完了整部书稿,我为他的传记写作精神所打动。合上书稿,我不免陷入沉思。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浮现眼前,似乎从书稿中走了出来,竟然那样鲜活、真实。与践耳先生几十年交往与合作的情景,一一浮现眼前。
书稿内容翔实、笔法细腻,语言简练、流畅通顺,读来很是亲切。秉承了他作传的一贯宗旨,即如他所说:“一位合格的传记作家,应具有太史公精神,不媚不俗、不阿诀奉承,不畏强权、不闻铜臭,秉公客观……”这种写作精神贯穿在全书中,这也是我最看重的传记应有的品质。
书名为《追梦者——朱践耳传》,很贴切。这并非时髦用语,而是出自践耳先生的自我总结。传记中写道:“朱践耳一生活在梦中,如他所说,‘从“革命梦”和“交响梦”之间,不断地来回徘徊,相互交替……’这注定他将成为一个追梦者……”的确,践耳先生一生,从未离开“梦”。
践耳先生是位天才音乐家。在去莫斯科留学前,他从未正儿八经学过作曲,但已经创作过许多好作品。他是一位旋律大师、和声大师、管弦乐配器大师,他的听觉尤为立体,甚是敏锐。为了艺术追求,他一生锲而不舍,心无旁骛。这是多么与众不同的可敬可叹的品质啊!
故此,雪钧先生即在目录章节中,将他的一生归结为“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三个阶段。有了这条主线,整书的章节,一气呵成地贯穿至终章。我认为,这是传记作家对作曲家有了透彻的了解和分析后,最严谨、最客观的归纳。
人非圣贤。作为一个有思想、有个性、有创造力的音乐大家,践耳先生一生,追求过、随流过、失落过、怀疑过、反思过,乃至晚年的回归自我。在人生的各个历史时期,践耳先生所走过的路,极不寻常。传记对这一切,没有回避,而是作了真实客观的交代。
譬如,在“失落自我”这部分中,传记引用了朱践耳先生对于严肃音乐深层面的剖析:“……说句实话,‘严肃音乐至今还未进入国家主流意识层面,以及通俗远胜于高雅’的文化特征,不仅20世纪50-60年代如此,进人新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如此。我国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也可见一斑了。”尽管他心里深感失落,但对“交响梦”,他依旧心存幻想。很快,由于形势发生变化,作曲家的思想开始变,放下了“交响梦”,去实现“革命梦”。
然而,在“回归自我”这个阶段,传记用了大量篇幅,详实记录了中国音乐界罕见的、勤奋有为的作曲大家。
……
这颇有些传奇色彩。朱践耳先生终其一生都在创作,且作品颇丰——11部交响曲、17部管弦乐、15部室内乐、8部声乐作品。特别令人惊叹的是,60岁以后,他用22年的时间,创作了10部交响曲。在近70年的创作生涯里,他涉足几乎所有体裁,留下许多音乐佳作。
我这55年的职业生涯,见证了中国交响乐近几十年的发展。指挥演出的作品,涉及256位中外作曲家,国内作曲家就有134人。但我指挥作品最多的中国作曲家是践耳先生,我与他是不可分割的。
1986年,我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北京音乐厅首演他的《第一交响曲》。不少听众由于是第一次接触现代作品,有些无法接受,但这并不妨碍这部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涵轰动乐坛。这时,一个民间组织-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对朱践耳的《第一交响曲》开展研讨,给予朱践耳极力支持和巨大鼓励。紧接着,朱践耳又创作了《第二交响曲》。这部作品采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乐器——锯琴,充满了悲剧力量,也是我最喜爱的朱践耳作品之一。
就这样,他每写一部新作,我就指挥一部。每次排练时,我请朱践耳上台给乐队讲作品的内涵和情感。试奏的时候,发现个别地方演奏效果不理想,就建议朱践耳修改。有些意见他会接受,但有时候他也很坚持。
朱践耳也会给我“出难题”:他的《第五交响曲》,需要用五十多件打击乐器,我们四处寻找,有的还要自己制作; 他的《第十交响曲(江雪)》,作品非常有创造性,其中有京剧的吟唱,古琴的琴音,演出中还要放录音,节奏必须指得非常准,稍有差池就会出岔子,演出的压力极大,可以说,这是我指挥过的最难的交响曲之一。我敢说,朱践耳先生的这部上乘之作,在首演后,再少有指挥家愿意冒“翻车”风险而搬上音乐会。
这也是人们常常感到奇怪的地方:践耳写了不少精品之作,但除了个别几部交响曲之外,其他作品似乎并不走运。多部作品首演之后,再无上演机会,被丢入冷宫。朱践耳的显赫名声,似乎还停留在《唱支山歌给党听》那首歌曲上。
这一切,朱践耳并不在意,他似乎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2015年9月,上海交响乐团重新演释《英雄的诗篇》。我跑到上海图书馆,找到朱践耳当年的手稿,熬夜写伴奏谱和合唱谱。演出结束后,我在一本朱践耳《创作回忆录》的扉页上写下一段话:“我最为崇敬的大作曲家朱践耳先生,以及他的最伟大的夫人舒群女士:今晚终于圆了这个梦。”巨作《英雄的诗篇》在上交音乐厅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歌剧院合唱团演出了!好评如潮!
但谁又知道,这部中国交响乐史上可谓思想性、艺术性极高的上乘之作,自1990年获奖以后,除首演外,没被任何乐团演奏过第二次。对此,晚年的朱践耳,耿耿于怀,心有不甘,而传记准确地记录这感人肺腑的一刻。
在与践耳先生合作的几十年里,我深切地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一个温文儒雅的人,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人。
践耳先生的晚年,令人噓。这位以肖斯塔科维奇为楷模的作曲大家,直至耄之年,还心存终极梦想——期望写出15部交响曲,然而,命运却无情地捉弄了他。
但是,“六十岁学吹打”,朱践耳先生创造了中国音乐史上一个传奇:他不仅完成了创作上的美学转型,从传统乐派跨入了现代乐派行列,而且在交响乐的创作理念、母语运用、现代新技法结合上,成为具有现代意识、鲜明民族气质的一代大家,成为现代中国音乐史上教科书般的存在。
我相信,《追梦者——朱践耳传》,会成为研究朱践耳先生“为人从艺”的最为可靠的、真实客观的、有研究价值的史料。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