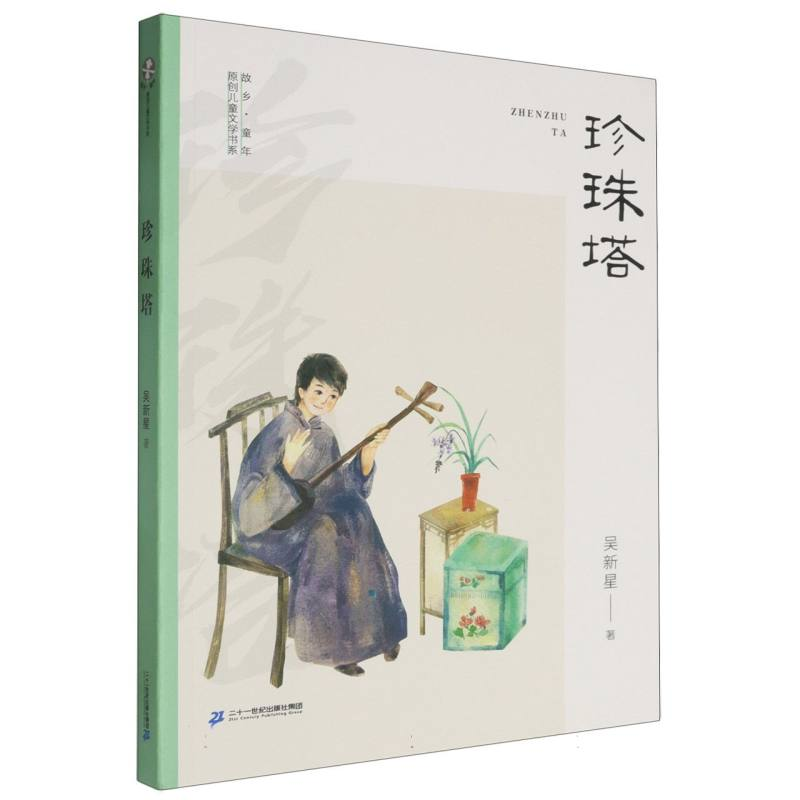
《珍珠塔》,吴新星 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24年7月
“苏州”,慢慢地念出这两个字,只觉有一种别样的温柔缱绻。苏州令人向往,“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苏州应该是这样的,温润、静婉、闲适。
对苏州,我怀了一种很深的情感。在写作的时候,常不自觉地把场景设置在苏州——其实,这些都是我的“一厢情愿”, 我只是它的一个过客,只去过一回,停留短暂的三天。
《随园诗话》有《题背面美人图》:“美人背倚玉阑干,惆怅花容一见难。几度唤他他不转,痴心欲掉画图看。”苏州对我来说也许就是这样的吧,它不是我的故乡,关于它的一切,我都感到不熟悉。它就像一个背面美人,呈给我一个背影。但就是这个背影,是那么的美丽与神秘,叫我愈加“痴心”。
在我的眼中, 苏州的一切也都是那么有意思。我写过苏州的卖花声、苏州的木屐板、苏州的梳头姨娘……总之,只要关于苏州,再细碎的事物我都喜欢。遑论苏州评弹了。苏州评弹,就像美人头上夺目的珠钗,光华熠熠——“苏州评弹与昆曲、苏州园林一起,成为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文化三绝’。”
说起最早与苏州评弹的因缘,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邀请了苏州的专业人员来演出评弹《雷雨》,整场演出,我从头看到尾,看完了还意犹未尽。原来之前纸面上的“评弹”,可以这么鲜活,这么美!
苏州评弹,美在吐字行腔。“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总称,是采用吴语徒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说书戏剧形式。”那一口如呖呖莺声的糯软的苏州话,叫人不由得沉醉。我虽然听不懂,那有什么关系呢?就像有人不懂粤语,却还是如痴如醉地聆听粤语歌曲。更何况评弹亦有不同的派别——评弹中常称“调”,有的深沉委婉,有的清丽圆润,有的铿锵明快,衬着弦琶琮铮,真个悦耳动听。
苏州评弹,美在遣词用句。我听评弹的时候,得借助字幕的帮助,所以对所唱之词格外留心。评弹里的唱词,随便摘录三两句就是一阙“绝妙好词”。比如《情探·梨花落》这一句:“梨花落,杏花开,桃花谢,春已归,花谢春归你郎不归。奴是梦绕长安千百遍,一回欢笑一回悲,终宵哭醒在罗帷。”唱词中的女子等到花开花又落,失望怨艾中难掩她的痴心。唱词有宋词般的蕴藉优美,又有民歌的直白晓畅,令人低徊不已。又如《珍珠塔》中引用的《剑阁闻铃》“峨眉山下少人经,苦雨凄风扑面迎”,这一句太像诗,容得起细细玩味,环境的凄苦实则是内心的写照,如此环境如此心境,真惨人也!下一句的“逍遥马坐唐天子,他是龙泪纷纷泣玉人”,语言风格则通俗多了,但是再怎么坐着“逍遥马”,坐马之人神情委顿至极,“龙泪纷纷”,与天同泣。
当然苏州评弹的美,远不止这些。演出的先生,只要坐在那里,那一种端庄优雅的气度,毋庸开口,就已叫人折服。我曾在小说《萧萧杨柳》中描绘过一位说书女先生:“那女先生身着藕荷色旗袍,上有流云似的图案;耳朵上一对半圆的珍珠,手上一只玲珑玉镯。那只玉镯随着她拨动琵琶,衬着身上的流云,如一只青鸟出入云端,隐约可见青色的一痕。”
从那时起,我的小说中常出现评弹的影子。《青丝剪》中,女孩绿萝的母亲就喜欢听评弹,我还把“徐丽仙”这个名字放在里面,因为她是我爱听的《情探·梨花落》的演唱者。《苏三不要哭》里男孩林瑞生“没事了就听无线电,妹妹们也过来一起听”。《萧萧杨柳》里女孩阿三的爹连在劳动的时候哼的也是评弹:“阿三一看,爹挑着藕担在前面,仿佛仍旧挑着空担一般,步履轻快。爹还哼了起来:‘一篙点破碧琉璃,轻舟摇出柳荫溪……’哈哈,是《三笑》里面《载美回苏》的一句唱词呢。”
只在笔下闪现篆烟似的一缕两缕飘忽的身影,我感到远远不够。我要围绕它写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在我的脑海中,依稀有了一个学评弹的男孩的身影。其实于“评弹”我是外行,全凭着一腔“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兴趣。现在要把“评弹”写成故事,我只有查阅跟评弹有关的资料,搜集跟评弹有关的书籍。在资料的收集与查找中,评弹少年的故事在我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很多时候,一边写着故事,电脑里一边循环播放着评弹的选段:《情探》《宫怨》《人面桃花》《剑阁闻铃》……听着评弹,恍惚自己身处苏州的某条街巷,耳边不经意间听到了这美妙的旋律。这是一次愉快的写作过程。
想起今年暑假的时候,见到林彦老师,我们交流起写作近况,他得知我写了一本关于评弹的小说,有些感慨地说:“倒是你这个外乡人写了。”我只是微微地笑。这一切只能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吧——我们村里的公园有一块文化墙,有一个版面是介绍本村的姓氏,其中有一行文字:“陈姓,始祖为晋时陈素峰,其从苏州枫桥迁至鄞县,居住在姜山,本村属此派系。”我的母亲姓陈。原来母亲的远祖居住苏州,千百年后,骨子中流淌的苏州情缘,在我这儿得到了遥远的回响。
我写苏州,写苏州的评弹,也只是藉此抒发对苏州这位美人的相思之情,只恨我非阿侬生小住苏州,我只能“魂牵梦萦到苏州”(周瘦鹃诗)。魂梦无据,唯有下笔写评弹,评弹声里寄相思。
延伸阅读|好书推荐:《珍珠塔》